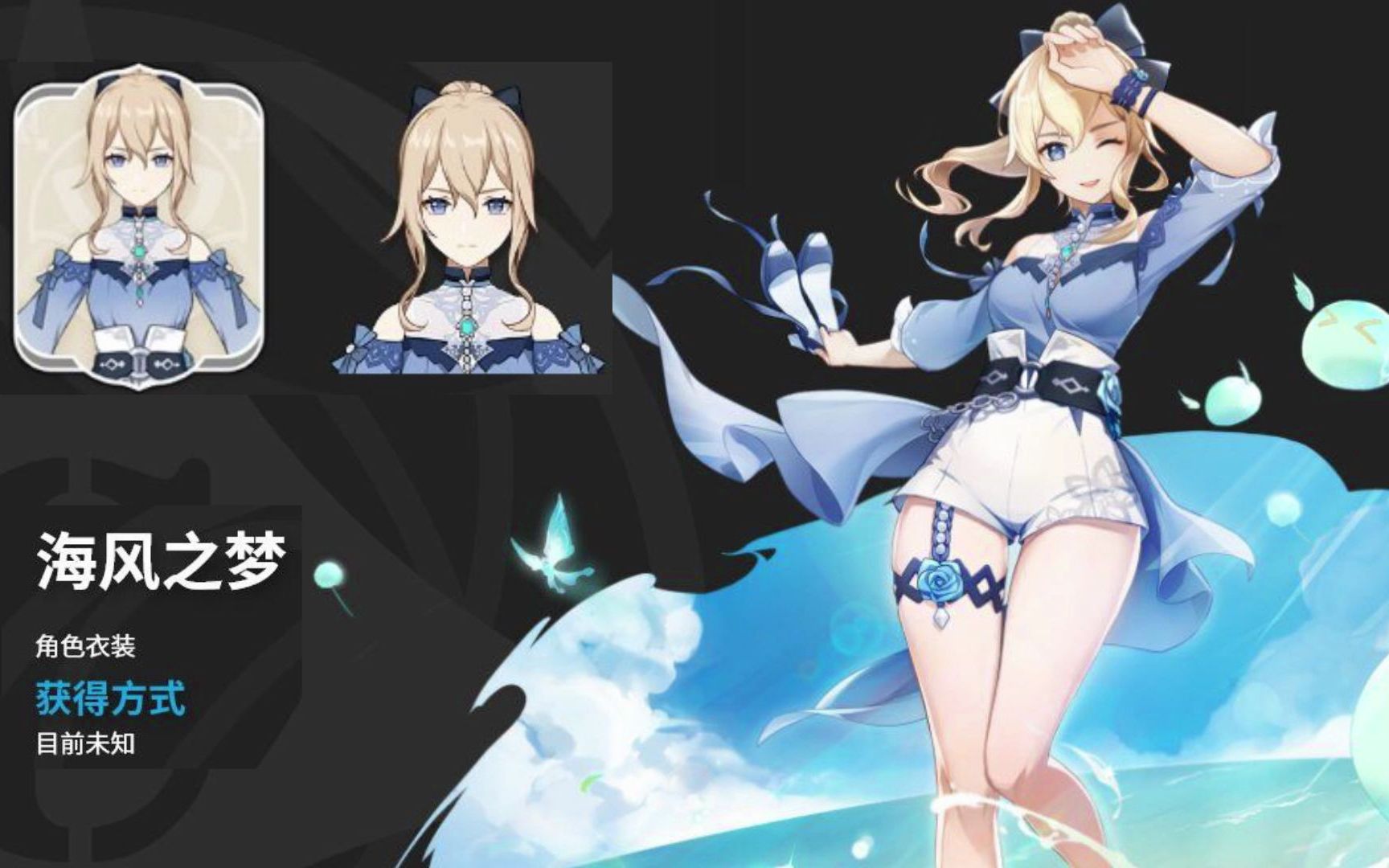原神里万叶,原神吧万叶
九块九推荐官 2023-05-25 03:10 124 浏览
侠世界微信公众号,中国最好武侠自媒体
刀剑江湖:工作日推送精彩原创武侠小说
《今古传奇·武侠版》邮局订阅代号:38-370
血月沧溟
文/莫缱
(大陆新武侠作家)
断雪
西安府,乍暖还寒。
早春风起,沧溟山庄里纷纷扬扬的不光是柳絮杨花,还有纸钱、为山庄主人君承宇而撒的纸钱。江湖上至今还有人不相信这个消息——四十七岁的西南剑盟盟主,如日中天,死亡离他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然而君承宇的确是死了,死于自家后院的庭树下,胸前有一处剑伤。他全身的血液便是从这伤口奔涌而出,流得一滴不剩。
如果原神吧万叶你听过“唐门掌门死于暗器”之类的黑色幽默,便能理解剑盟盟主被人一剑穿心的耻辱。那耻辱是死人的,也是活人的,属于沧溟山庄,更属于整个西南剑盟。
葬礼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进行着,隆重而沉闷。没有鼓乐,没有道场,没有礼节性的号啕或者啜泣。吊客们匆匆而来、匆匆祭奠、又匆匆离开,仿佛在躲避着什么不祥或者尴尬的东西。
君行远没有遵循孝子之礼在堂前守灵,他不愿意披麻戴孝地跪在那里,向不相干的人展示自己的悲哀,而且有些比守灵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思考——比如父亲胸前诡异的剑伤,和这剑伤引发的诸多传言,以及……
外面忽然有人叩了几下门。
总管孟于飞走进来,几天的忙碌使他看上去又憔悴了不少,整个人也是不胜衣冠的清瘦。他一双眼睛虽然仍温和有神,但两鬓却似在一夜之间就染上了秋霜。
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悲怆,逝去的君承宇不但是他的师兄,也是他三十几年倾力辅助的挚友。
“孟叔,你的头发……”君行远说。“朝如青丝暮成雪?”孟于飞苍凉一笑,“人生苦短,生死也不过朝暮之间。其实原神吧万叶我早就老了,只是因为有你父亲在,才没有觉得人生无趣。孟某这一生有九成的事情是为他做的,可是现在……我还能做什么呢?”
“孟叔不老,也并非无事可做,”君行远冷冷道,“至少,你还可以告诉我一些关于血月剑的事。”孟于飞目光一滞:“你怎么知道那一定是血月剑?”
“原本只是猜测,现在却几乎已经确定了。”
“……何以确定?”
君行远看着他:“是你的表情告诉我的。”
与多年来那些缥缈的传闻相比,孟于飞所知关于血月剑的事要简单许多:这套邪异的剑法并非沧溟山庄的武功,它只是随着一个外来的少年而来,在沧溟山庄里存在过一段时间,然后又消失了。
带那个少年回来的人,是君承宇和孟于飞的师父、沧溟山庄的创立者——龙九霄。三十几年前一柄独步天下的九霄剑,成就了他的英雄神话。而那时,孟于飞还只是个孩子。
龙九霄一生有数不清的对手和仇敌,他堂而皇之地战,堂而皇之地杀,既然所有的事都在光明处进行,便该胜者无愧、败者无怨,因此在遇到江秋水之前,他从不替倒下的人惋惜。
与江秋水一战却让龙九霄回味了十三年,也遗憾了十三年,一直到死。因为决战之后他才知道,江秋水其实已经身患绝症,否则凭借他那套奇诡的“血月剑法”,胜负尚未可知。
决斗后返回沧溟山庄时,龙九霄的身边多了一个男孩儿,那是江秋水七岁的独子。孟于飞至今还记得那孩子初来时的模样——苍白如雪的衣裳,苍白如雪的脸色,眼睛却不同寻常的黑,幽幽地扫视所有的人,似乎在留意着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没放在心上。他的名字叫断雪。
十三年后龙九霄病逝,弥留之际将一幅写满字的冰绡交给了断雪,那便是血月剑谱——江秋水的临终之托。
龙九霄的最后一句话是:“江秋水,我总算对得起你。”
随之而来的葬礼成了当年江湖上的绝顶大事,然而就在下葬的前一天晚上,断雪忽然不知所终,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那幅血月剑谱。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离开,去了哪里,只有一些关于血月剑的描述被人们口耳相传,全都离奇得不着边际。
“我从未见识过血月剑,”孟于飞说,“只是知道,这是种戾气十足的剑法,一剑夺命,且中剑者必然滴血无存,就像……”
“就像我爹一样。”君行远冷冷接口。
“……这只是我的揣测,但除了血月剑,我没有听过第二种可以做到滴血无存的剑法。而除了江断雪,血月剑也再没有其他传人。”
“江断雪是个怎样的人?”君行远忽然问。孟于飞沉吟片刻:“说不清……除了你娘之外,当年几乎没什么人可以接近他。”
“我娘?”
孟于飞苦笑着拍拍额头:“险些忘事——我来,正是想叫你去看看你娘,有下人说她在后院的风口里,已经站了两个时辰了。”
桃花
整个上午,龙夕都在看一株桃花。那花蹊跷得很,前几天还不见动静,今早却忽然顶了料峭的春寒开出满树妖娆来。龙夕一袭薄衫站在树下,玉雕般淡雅安静。
君行远叹了口气,解下披风披在她身上——这个女人可以学着别人的样子,将儿子潦潦草草地养到十八岁,却至今都学不会照顾自己。
“桃花有那么好看么?今天这样的日子,至少你该去灵堂呆上片刻。”
“你不是也没去么?”龙夕头也没回,“这花开得好艳……他走之后,还从没有这样开过呢。”
“他?”
君行远知道母亲又在想从前的事了,或许根本就与桃花无关。她总有这样的本事,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能忘了今夕何夕,自顾自沉溺于遥远的往日时光中。似乎有个人的影子始终在她心头盘桓不去。君行远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却能够肯定——那人决不是他的父亲。
“我有一些旧事要问。”君行远不得不将她的思想拉回来,“多年以前有个叫江断雪的人,你还记得么?”
多年以前,一样的早春,一样的风,春寒,桃花。
那时候父亲龙九霄还在,天真烂漫的少女心性还在,江断雪飘忽的白衣还在……那时候,沧溟山庄还是龙夕的家。
江断雪在沧溟山庄像个孤独的异族,龙九霄视同己出的关怀也不能化去他身上那层似乎与生俱来的阴郁和冷漠。平静而疏离的态度将他与众人隔绝开来。他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封闭空间里长大成人,能够且愿意走进这空间的,也许就只有龙夕。
与诸多闻鸡起舞的师兄弟相比,龙夕活得过于自由散漫了些。她的脚步永远追逐着自己的兴趣,而放眼整个沧溟山庄,江断雪就是她最大的兴趣所在。从小到大她对这个人有着太多的疑问。比如——
“你到底恨不恨我爹呢?”一起看桃花的时候,龙夕忽然问江断雪。十余年来这个问题她问了几百次,却从没有得到过明确的答案。
“很重要么?”江断雪懒懒地反问,阳光里只一袭轻袍的背影白得几近透明,“寄人篱下,是没有资格谈恨与不恨的。”
“那你会离开么?”
“现在不会。”
“什么时候会?“
江断雪笑了:“下次不要再问这些无聊的问题了。”
于是龙夕也懒得再问——至少现在他还在这里陪她看花,明天的事,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那个春天,桃花将残未残时,龙九霄身染重疾。龙夕亲眼目睹了曾经叱咤风云的父亲,由健康到病弱、直至死亡。她突然明白了人生无常,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的。之后的几个晚上,她都在冷月下痴坐,听着江断雪幽咽的笛声,直到东方欲晓。
“你现在还恨我爹么?”仍旧是老问题。
“恨。”江断雪的回答却前所未有地干脆。
“……他已经死了。”
“所以我才恨他,”江断雪怪异地一笑,“他给了我血月剑谱,却不肯给我一个战胜他的机会——这世上没有了龙九霄,血月剑还有什么意义,我在这里十三年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龙夕第一次直面江断雪的怨恨和野心,那双幽深的眼睛里有些东西让她感觉很茫然——取回血月剑谱,战胜龙九霄,这就是他留在沧溟山庄十三年的理由?
“除了血月剑,沧溟山庄就再没有什么让你留恋了么?”
“有。”
“是什么?”龙夕问。
江断雪温柔地望着她:“你说呢?”
然而数天后江断雪还是走了,带着他的血月剑谱,像水滴蒸发在空气里。其实长久以来龙夕就知道,这个人在沧溟山庄终究只是个过客,却没想到他会离开得这样突然、这样彻底,彻底到居然连一句告辞的话都没有留下。
守孝期满,龙夕嫁给了龙九霄的首徒君承宇,沧溟山庄自此易主。那是一段江湖称道的金玉良缘——青梅竹马、佳人俊杰,这样的故事每个人都愿意听。
“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君行远顿了顿,“还是知道,却不想告诉我?”
“我不知道。也许他在什么地方练剑吧。他说过,要领会血月剑,似乎需要很久呢……”
“久是久了一点儿,不过现在似乎已经成功了呢。”君行远冷冷地笑了,“现在龙九霄最得意的**已经被他一剑击杀,血月剑……好剑!”
龙夕的眼神淡若轻烟:“你以为是他?”
“如果是他,你会怎样?”君行远反问,“如果有一天我们遇上,你是会帮我杀了他,还是帮他杀了我?”
龙夕回头望着儿子,却忽然发现他的个子已经很高了,自己要仰视才行。
“小远,”她喃喃地说,“你长大了……”
红影
君承宇下葬后七日,西南剑盟各派龙头云集沧溟山庄。这本该是一次新盟主就任的会议,但开着开着却变了味道。偌大的厅堂中数十人如泥坯木雕般陷入沉默,到后来,连空气都仿佛凝滞了。
君行远忽然想笑,冷笑。眼前一张张欲言又止的尴尬面孔让他感觉有些滑稽。他知道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西南剑盟建立至今,执牛耳者始终是沧溟山庄,那是因为龙九霄和君承宇两代人杰的实力威望。而现在,故人已矣,谁还愿意再去听一个未及弱冠的孩子号令呢?
所有的腹诽和争论都只隔了一层薄薄的面皮,君行远想起父亲督促他练剑时常说的一句话:“再显赫的家世也不能帮你一生,有朝一日人走茶凉,只有这把剑才是真的。”
轻咳了一声,他决定还是由自己这无知后辈来将话挑明——能大胆地说出一些长辈想说、却又不敢说,不屑说,不好说的话,这就是小孩子的好处。
“虽然外祖和先父连任了两届盟主,但西南剑盟初建时就有约定:盟主一职唯有能者居之,而非世袭。”君行远扫视了一眼众人,“行远年少,这担子太重了些,所以斗胆请诸位赐教,如果谁能胜了我手中剑,就请代为接任盟主,行远将不胜感激。”
许多人听到最后才知道他是在挑战,旁边的孟于飞一声轻叹,又忍不住微笑——这个孩子到底像谁呢?外表的谦和冷静显然承袭于父亲,而骨子里的孤直好胜却又与他那不可一世的外祖何其相似啊!
君行远击败第十三个挑战者的时候,白麻布的孝服上又多了一道血色的口子。极少有人能在半日之间集十余种不同风格的剑伤于一身——就算有实力,也未必能凑得这么齐全。这场“点到为止”的车轮战让他受益良多,至少明白了在争夺权力的战斗中,永远也没有“点到为止”这回事。
所以几轮挑战后他开始下重手。血在流,但剑却越来越张狂无忌,也不再去挂怀又伤了哪位世叔世伯,仿佛这世界上就只剩下两种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太阳快要落山了。
“还有没有人?”他问,手中一柄透着上古遗风的重剑斜斜指向地面。
死寂。空气里飘荡着阴郁的血的味道,之后有人开始向他俯身施礼,一个、两个、三个……所有人都向他俯身施礼。
太阳真的落山了。
人群散去,空旷的院落就显得更加空旷,浑身的伤开始作痛,痛到有些麻木。但这对君行远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从小到大在父亲的督导下苦修,所受的剑伤鞭伤早已不计其数。十几年来君承宇对于儿子的严苛常常让一些不相干的人都觉得残忍,不过现在看来那似乎是对的。明天开始,西安府的茶寮酒坊里就会有新的段子流传:沧溟山庄少主人一剑独挑十三剑派,历史上最年轻的剑盟盟主走马上任……诸如此类。这场胜利将会让他在一夜之间闻达于天下。
君行远在冰凉的石阶上枯坐了一个时辰,再抬头才发现已经是皓月当空。他忽然想去看看母亲,听她说几句话,那是种没有理由但很强烈的冲动,让他觉得自己只是个孤独的孩子。
是不是人在夜里、在遍体的伤痕之下,总是会觉得比较孤独呢?
龙夕住的小楼坐落在后院一片竹林深处,沿那条泛着月光的青石小径走过来,隔着疏疏落落的竹子就可以看见楼上的灯火。君行远知道母亲的习惯,这个时候她一般是不会睡下的,然而还没等他走到小楼前,却看见那灯光忽然熄灭了。
君行远停住脚步,在竹林的阴影中静静观望着那座小楼,直觉告诉他似乎有事情要发生。片刻之后有人影从里面出来,是两个,悄无声息地走向通往山庄后门的小道。借着月色君行远看得很清楚,其中一个正是母亲。
龙夕不是个好动的人,十几年来她几乎没去过沧溟山庄以外的地方,更何况是在夜里。君行远本能地跟了上去,然而才走几步,与龙夕同行的那个人却蓦地返身飞扑而至。
窈窕而轻灵的影子,月光映出水红的裙袖和一支冷冽的长剑。在躲过剑锋的一瞬间,君行远至少确定了三件事:这是个年轻的女子,以前从未见过,武功不弱——至少不在白天与自己交手的任何一位掌门之下。
红影飘落在一丈开外,淡淡的语声中透着些孩子气:“你,什么人啊?”
君行远怔了怔,这个问题似乎该由自己来问才对。然而对方却不打算让他开口,红衣飞舞间又是一剑刺来,用的居然是……沧溟山庄的九霄剑法!
太多的疑问反倒让君行远不再去质问。与其在交手的时候废话,还不如把她捉住再问个明白。于是重剑挥出,刚劲的力道之下,那迎面而来的一击硬是被撞了回去。水红色身影踉跄退了几步,忽然一声轻叹:“我记住你了……”话音未落长剑脱手掷来,人却凌空倒纵,掠入斑驳幽暗的竹影深处。寂静重又笼罩了整个竹林,长夜中空剩一片月华如水,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只有那柄弃剑还在地上躺着,龙夕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落花亭
“有这个必要么?”孟于飞拿了一份追缉令匆匆来见君行远,“她是你的母亲。”“那又如何?”君行远无动于衷,“她去了什么地方?”
“用追缉的方式?这样会惊动整个西南剑盟。”
“就是人多才好办事,至于颜面……沧溟山庄积攒的那点颜面,反正已丢得七七八八了。”
孟于飞有些无奈地掉转话题:“那个红衣女子,你确定她用的是九霄剑法?”
“我确定。”
“但九霄剑法在沧溟山庄以外是不可能有传人的。”
“孟叔真的忘了么?当年从我外公那里学了九霄剑法的,除了您和我爹之外,据说还有一个人。”
孟于飞怔住,许久才轻轻一叹:“江断雪……”“是的,江断雪。”君行远点头,“这样一来事情就说得通了。为什么我娘会出走,为什么那个女子会九霄剑法……现在我需要整个西南剑盟来帮我找人。”
君行远相信只要找到龙夕或者那个女子,就等于找到了一切,却没想到三日之后,他要找的人会主动来找他。
“明日破晓,渭水落花亭,带剑。”
那天清晨门丁送来这张寥寥数字的锦笺,没有开头没有落款,但君行远知道,这是写给他的。
落花亭外无花可看,能看到的只是荒山野草,还有那条浑浊得天下闻名的渭水河。至于为什么叫落花亭,没人去探究,反正天底下名不副实的东西又不止这一件,何必认真呢?
日出之前天地间弥漫着浓重的江雾,君行远独自一人提剑而来,袍袖被打得有些湿了。离落花亭不足百步时才隐约看见凝立其中的人影——水红色,眼熟得很。
“你的剑还在我家。”君行远说。
“那把剑输给你了,我不要。”亭中的水红色幽幽回应,“我们今天再打过。我换了柄和你一样的重剑,这次一定可以胜你。”
“是么?”君行远一笑——如果换剑能解决问题,又何苦练剑?不如去做铁匠。“你笑我!”水红色似乎有些生气,“出剑吧。”
“我不是大街上卖艺的,你叫出剑就出剑——就算是卖艺,也总要有些报酬。”
“……我没有钱。”水红色很抱歉地说。
“不用钱。”君行远苦笑,“你只要回答我三个问题。第一个,我娘在什么地方?”
“那个大美人么?在我叔叔那里。”
“你的九霄剑是谁教的?”
“我叔叔。”
“你叔叔是谁?”
“第三个问题了!”重剑破空的声音和那水红色的身影,在视野里骤然明晰起来,“他叫江断雪。”
尽管君行远对于这场较量本来并没有多大热情,但“江断雪”三个字仍然像颗火种,点燃了他的血液。三十余招之后胜负立分,那女子怔怔望着横在颈上的剑,而君行远也第一次看清了她的模样——十六七岁,有一双湖水似的眼睛。
“原来换剑也打不过你。”她说,湖水就漾出来……哭了。
过了片刻。又过了片刻。
君行远隐隐有些头痛,他从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可以哭上这么久,更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她停下来。
“你已经不错了。”等到抽泣声稍稍微弱了些,他终于忍不住开口。水红色的姑娘无言地望着他。
“……九霄剑本就不太适合女人,你能有这种成就,已经不错了。”
见过江眸儿那双大眼睛的人都得承认,“眸儿”这个名字实在很适合她。但在遇到江断雪之前,江眸儿并不叫江眸儿。当时她六岁,衣衫褴褛、插了根草标,被人贩子拖着当街叫卖。那种境遇下人命如草,而草自然是不会有名字的。
午时骄阳似火,弥漫长街的燥热喧嚣让人在绝望中委顿,又因为委顿而更加绝望。所以当一袭清冷的白衣从面前飘过,她忍不住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抓住了那人的长袖——很本能的动作,只是想留住一点冰凉的感觉。然而缘分是奇怪的东西,有时候际遇的转折也就在这样伸手一抓之间。
两双同样大而黑的眸子对视了片刻,那人忽然笑起来:“你想跟我走么?”
眸儿至今不太明白,像江断雪那样的人,当初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去收养孩子。十余年来他们从没在一个地方久留过——塞北、江南、京师、边城,甚至鞑靼人的草原,哪里都可以驻足,但哪里都不是家。似乎他有生以来就是这么漂泊着,而且还将继续漂泊下去。
只是人的一生,总要有个起始的地方吧?即使是江断雪那样的人,也总会有故乡吧?两个月前他忽然说要来西安府,于是就来了。但眸儿渐渐发现了一些异样的东西——从江断雪看这个地方的眼神里,从他缥缈的笛声中。
这里与以前到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呢,她想。
那天傍晚江断雪要眸儿去请沧溟山庄后院小楼上住着的人,原本以为要费些周折,但那个神情冷漠的美丽女子在听到“江断雪”这三个字之后,居然一言不发就跟着她走了……
“我真的没有胁迫你娘。”江眸儿诚恳地告诉君行远。这一点他是相信的,龙九霄的女儿没那么容易被胁迫。
“而且叔叔对她也很好,这几天一直陪着她,都没空理我。”江眸儿有些落寞地抱怨,没发现君行远的脸色已经隐隐泛青,“所以我才来找你比剑……”
“江断雪看家的本领,难道没有教你?”君行远冷眼看着她。“看家本领……”江眸儿的语声忽然停顿,皱着鼻子,品味什么似的深吸了口气,“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身上用的什么香料?味道……真特别。”
雾非雾
异香,似兰似麝,幽淡而妖娆地氤氲在湿冷的雾气里。那并不是君行远身上的味道,他素喜清洁,可还没到涂脂抹粉的程度。
“我从不用香料。”君行远看了江眸儿一眼,“不是你身上的么?”
两个人忽然沉默了,异样的感觉开始在心底蔓延——那幽香切切实实地存在着,而视野所及,能看到的却只是草地、河水、没有花的落花亭……还有淡淡的雾。
蓦然间穿云裂石的一声长哨,几条灰色人影带着激飞的水花自渭河中冲天而起,湿淋淋却又悄然无声地翻落在河岸上。想来他们已经在水下潜伏了许久,满是泥浆的衣衫看上去有些狼狈,眼神却冷厉如鹰。君行远数了数——十个人。十个人,十把剑,安静得近乎阴森地列成一排。
“江断雪叫来助兴的?”君行远讥讽地回望,却发现江眸儿正以剑撑地,脸色苍白如纸。还没等他开口询问,深深的无力感就席卷了四肢百骸,一向稳如磐石的右手竟然有些握不住剑。
浸透晨雾的幽香仍在萦绕,很温柔,温柔得能杀人于不知觉间。既有这杀人的温柔,还安排下这么多杀人的利剑,看来对方是下定决心了。
“谁让你们来的……要对付的是我,还是他?”江眸儿忽然问,无论什么时候,她的好奇心总是占着上风。
灰衣的杀手们默然凝立着,片刻之后其中一人才吐出三个字:“都一样。”“都一样”的意思就是——反正也没打算留活口,何必计较那么多呢?
君行远出剑的时候没有犹豫。灰衣人的按兵不动其实是在以逸待劳——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力量正随着那勾魂蚀骨的异香从自己体内消失。再不出手,最后只会变成一块毫无抵抗能力的绵软鱼腩。
重剑带着撕裂风雾的锐啸横扫过去,君行远冲入重围的身影像一头桀骜不驯的豹。夕阳晚照有时会格外耀眼,那是因为残存的能量聚集起来,在做最后一次勃发。对手眼中闪过的讶异更激起他的斗志,身边忽然又多出一个并肩作战的影子:江眸儿,苍白着一张小脸,水红色的衣衫在剑意江风里猎猎飞扬。
这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艰难、最无望的一场战斗,但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顽抗到底。
鏖战中雾渐渐淡了、散了。旭日升起来,明艳的光线照着露水晶莹的草滩和滩上厮杀的人。君行远强弩之末的精力已经很难支撑九霄剑那磅礴的剑势,他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秒就会倒下。一旁江眸儿的步法则更凌乱,像是喝醉了酒。君行远不得不耗费更多气力替她挡下头顶劈落的乱刃。
突然,一叶扁舟从江上过,雪色轻袍的男子站在船头吹一管长笛。笛声如北风呜咽,悲怆低徊,不经意间就摄了人的心神去。
“叔叔……”
意识丧失之前,君行远听见江眸儿微弱地轻唤了一声。
北郊,驿道旁门可罗雀的一处野店。
君行远醒来时已经天近黄昏,而且,是第二天的黄昏了。一抹残照泻进西窗,笼罩住床边斜坐的温柔侧影——龙夕。
“好久不见……”君行远说,或许是虚弱的关系,几天来纠结于心的忧虑和怨气就只化成这淡淡的四个字。
而龙夕眼中则明显有了些释然的意思,伸出一只手探上儿子的额头:“我还以为你会死,但是他说只要能醒过来,就没事了……”
“他?”君行远的微笑苍白而痛楚,“江断雪么……以前你可从没用这样的语气称呼过父亲。是他救我?”
“是。”
“可我还是会杀了他,或者被他杀死……你更希望哪种结局呢?”君行远问龙夕,心却被深深的悲哀包围着。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哪种结局,眼前这个他称之为“母亲”的女子,都不会再属于父亲,不会再属于沧溟山庄了。
龙夕感觉到他的悲伤,一声轻叹中不知是怜惜还是无奈:“你爹在你心中是最优秀的人,对么?”“没有人比他更优秀。”君行远说,有生以来他从未怀疑过这一点。
龙夕沉默,望着什么地方静静地出了会儿神。
“江断雪在隔壁等你,要是想去……就去吧。”
夜深沉
日薄西山,天际还有一抹残霞未尽。然而当君行远推开隔壁那扇虚掩的门,竹榻上倚坐的白衣男子已经点燃了一盏纱灯。
“我不大喜欢黑夜。”他说,一双眼睛却比黑夜更加深邃。“我也是,”君行远将剑横在面前的条案上,“因为我父亲是在夜里被杀的。”
短暂的沉寂,然后江断雪淡淡笑了:“你和你父亲不大一样。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没有这样锐气逼人……至少看上去没有。听说你是连胜十三个剑派,才掌管了西南剑盟的……”
“我对那群乌合之众没有兴趣,”君行远打断他,“不过是想多些人手来查找真凶,而且,现在已经用不着了。”
“你和君承宇真的不一样。”江断雪摇摇头,冷笑,“当初他为了能统领这群乌合之众,可是呕心沥血呢。”
“……什么意思?”
江断雪没有立即回答,眼神有些空洞地望着灯影摇曳,忽然问了句不相干的话:“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黑夜么?”
龙九霄下葬前的那个晚上,江断雪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灵堂见死者最后一面——与恩怨无关,只不过龙九霄的样子已经在他心里刻了十三个年头,少看一眼也不会忘。所以他宁愿在后院的湖石上枯坐,遥想着那个曾英雄盖世、现在却安静地躺在棺木中的人;那个杀了他父亲又抚养他长大,还将自家剑法倾囊相授的人;那个他唯一仇恨又唯一崇拜的人……
风很凉,然而更悲凉的是心情。月光时隐时现,夜空里飘浮着妖异的黑色云朵。云在白天或许是美丽的,但晚上看上去,却只让人觉得狰狞恐怖,更恐怖的是——你分不清美丽与狰狞,哪一个才是它本来的样子。
异样的感觉忽然打破了长而凌乱的思绪,江断雪确定在身后有双眼睛正看着自己。他回过身的时候,月光刚好照上不知何时站在那里的君承宇和孟于飞,两张原本俊朗的脸在那样的光线中居然有些阴森。原来很多东西在夜晚都会变得面目可憎,不光是云而已。
“有事?”江断雪问,十三年来他与他们的交谈一向简短。
然而这一次他得到的回答更简短,简短到没有一个字,简短到只是长剑出鞘的声音……两支剑,一上一下,以同样的方式和速度刺入他的胸腹再抽离出来……利刃冰凉、阴寒彻骨。
剧痛袭来之前,江断雪选择了后退,无言地、疾风般竭尽全力地后退。尽管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而毫无道理,但他却连一点惊怒或者恐惧的时间都没给自己留下。那份异乎寻常的敏捷果断使得两个猝下杀手的人也不禁微微一怔。就是在这样微微一怔之间,他的身影已经在数丈开外。
“龙九霄——你的外祖父,曾教过我很多东西。他说在遭遇暗算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问为什么,因为等你弄清了原因,只怕人已到了黄泉路上……”江断雪靠着竹榻,带了三分慵倦娓娓而谈,全不在意君行远煞白的脸色和紧握成拳的双手。
“我爹和孟叔……暗算你?”君行远淡淡地问了一句,竟笑起来,眼中却似有火焰喷薄欲出。
这是他有生以来听过最荒谬的谎言,可是自己为什么没有一剑挥去,却只是在这里冷笑?为什么笑声里除了愤怒,竟然还有一丝恐惧?是不是因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出了裂痕,开始动摇了?
“君承宇在你心中是个完人吧?”江断雪看了他一眼,语声里并没有讥讽的意思,反倒多了些温和。君行远沉默,同样的问题他刚刚已回答过龙夕。
“要是你高兴,一会儿仍然可以杀我,”江断雪笑笑,“我只告诉你我的一面之词,信与不信,是你的事……”
夜风回旋,轻柔得像龙夕的头发,渭水河在月光下奔流。岸边,站着摇摇欲倒的江断雪和执剑而来的孟于飞。
“只有你?”江断雪问,一襟冷月一襟血,却仍然透着孤傲。
“遇上岔路,师兄追去了另一个方向,不过对付已受重伤的你,只有我也是一样。”孟于飞说,还是一贯的温良平和,满心杀意都只闪烁在剑锋上。
江断雪知道凭自己残灯将尽的体力已经再不可能脱身,倒是也终于可以问一句为什么:“总要给我个理由。”
“师兄要杀你,我只是帮他。”
“君承宇?”江断雪苦笑,“我想不起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他。”“不是得罪,是威胁。”孟于飞耐心解释,“师父是个豁达的人,才会将血月剑谱交给你。而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同样豁达,不知道有了你和血月剑谱,沧溟山庄的命运将会如何,所以只能作最坏的打算……另外,还因为龙夕。龙夕是师父的掌珠,是唯一有资格继承沧溟山庄的人。师兄只有娶她为妻,才可以接手山庄进而掌握西南剑盟。换句话说,龙夕该是师兄的,而你和她走得太近了……或许十三年前你踏进沧溟山庄就是个错误,人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呆得太久,总是要招来灾祸的……”
“灾祸”二字甫出口,寒光飞泻的一剑已经当胸而来。江断雪没有闪避,只听着渭河的流水声。
忽然想起龙夕。这个时候,龙夕在做什么呢?
“异域有种鹰喜欢在万仞绝壁上筑巢,一巢二子。但最后能扶摇于天的,却只会是年长的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江断雪望着君行远,黑眸仿佛深不见底,又仿佛空无一物,“因为弟弟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被兄长当成了死敌,兄长无时无刻不想杀之而后快,一旦父母离巢,便开始穷凶极恶地推挤啄咬,直到将年幼的稚弟挤落悬崖或者摧残致死,它才能高枕无忧地独占巢穴,独享食物。到时便可羽翼丰满,一飞冲天……同胞手足尚且如此,这世上什么人向你拔剑,都是不奇怪的……”
“……你却没有死。”
“一息尚存,落入渭河,天快亮的时候,被下游野渡上的舟子救起,在那人家里养了许久的伤。然后……听到龙夕与你父亲成亲的消息……这并不坏,至少比和我这样的人流落江湖要幸福些。之后我便离开西安府,四处游荡、练剑……”
“练剑?”君行远想起父亲那鲜血流尽的冰冷身躯,那致命的剑伤,那犹自带着惊诧的青白的脸……眼前这个人苦心练了二十年的,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剑法?
“关于旧事,如果我能活着回去,自然会向孟叔求证。”他握住重剑站起来,剑在手,心却如止水。一些事情暂且抛开不想,而另一些事情已经想得通透,“现在我只想领教一下你的血月剑法,看看它到底强出九霄剑多少,才能将西南剑盟的盟主一剑毙命。”这一战原本就是在所难免的——即便没有杀父之仇,即便只是出于一个剑客的野心、一种渴望战斗的本能。
但江断雪却坐在那里没动,看着重剑的锋芒,忽然幽异地笑了:“谁告诉你血月剑一定强于九霄剑?谁又告诉你,我一定就是那个会血月剑法的人?”
君行远执剑的手僵了一下:“我不明白。”
“杀你父亲的人不是我,因为血月剑的剑谱根本不在我手上。这二十年来,长伴我身的始终只有九霄剑——沧溟山庄的九霄剑……你相信么?”
血月
四更月落,檐下几十盏灯笼燃起来,照着沧溟山庄偌大的中庭,很明亮,也很寂寥。孟于飞独自一人在庭树下徘徊,手中提了柄造型奇异的无鞘长剑。那剑是三年前他亲手所铸,铸成后却从未给人看过。剑号“同风”,出自于谪仙的一阕《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几乎没人知道沉静如水的孟于飞,居然也会喜欢如此傲岸轻狂的文字。
夜长风冷,孟于飞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久了便觉得有些无趣,却又不肯回房。刚想着这么大的庄院,实在不该过于冷清,身后便有一剑电掣而来。
孟于飞转身时寒芒已迫眉睫,劲风鼓荡起他的青衫,狂飞。他却伫立未动,只是同风剑在灯下忽然泛出些微光,淡淡的、竟透着绯色。
绯色的剑光,妖幻如血,苍凉如月,无声缠绕住袭来的锋刃,铿锵之间,星雨般的火花溅落……之后,两个人都停了手。
“方才那一式,就是血月剑法?”君行远问,重剑遥指着孟于飞的眉心,颈上却被“同风”划了一道浅伤,鲜红的血珠正缓缓渗成一线。
孟于飞有点儿忧郁地望着他:“从落花亭的伏击失败,我就没打算再隐瞒什么。只是你既见了那人,找到你娘,又何苦回来?”
“那人给我讲了个故事,很荒唐,却漏了最离奇的那段。”重剑垂下来,君行远看着孟于飞瘦削的脸,那脸庞原本比父亲还要熟悉而亲切,现在却和这沧溟山庄的庭院一样,变得陌生遥远起来了。
“我回来,只是想听孟叔把它讲完。”
世间万物,最无常的是命运,最古怪的是人心。亲与仇相距多远?生与死相距多远?朗朗乾坤与阿鼻地狱相距多远?有时候只那么一念之差,很多事情就万劫不复地变了……一念之差,差得又有多远呢?
还是那个晚上,轻风冷月、四野无人。孟于飞的剑已经没入江断雪的胸膛,只是位置偏了些——那年他未及弱冠,对于杀人,终究还算不得行家里手。血溅在身上的感觉很不舒服,迎面而来的血腥气更让人窒息。幸好事情快要结束了,渭河的泥沙会埋掉一切,明天太阳升起来,他仍然是沧溟山庄里温文的二师兄。三年五载之后,或许连自己都已经忘了这个月夜——人生近百年,抹去一个晚上又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自我安慰之下,孟于飞曾一度轻松了片刻——直到江断雪的衣袖中飘出那幅写了字,染了血,蝉翼似的白绡。
轻轻软软的一幅白绡,飘落在地时连声音都没有,然而却像一块投入湖水中的巨石,让孟于飞的心湖都波涛汹涌起来——这东西他见过一次,虽然只有一次,却是不会忘的。
“这个,就是血月剑谱。”江断雪说。
孟于飞望着江断雪的脸,那张苍白无色的脸上一抹稍纵即逝的诡谲微笑让他觉得很困惑——一个身中三剑、说话都费力的人,一个几乎已经成了死人的人,究竟在高兴些什么?
“你想用血月剑谱换回性命?”孟于飞冷笑,这样愚蠢的想法不会是他开心的原因吧?江断雪摇了摇头。“我还没有蠢到以为你会放过我。”他说,“只是不想让血月剑谱和我一样从世上消失而已……这也许是天下唯一能和九霄剑分庭抗礼的剑法,沉进江底太可惜了,不如,送给你……”
“……你说什么!”
“送给你……有朝一日你在君承宇身后跟得厌倦了,就会用得着的……”江断雪的声音很微弱,却一字一字传递得无比清晰。
孟于飞忽然明白他的意思,想冷笑,然而脸僵住了,没笑出来。
“我和师兄的感情,没你想的那么脆弱。”他咬了咬牙,长剑从江断雪胸口抽出。江断雪身子摇晃了一下,却无声地笑起来,幽黑的眼眸在夜中魅惑如妖魔:“那就让时间来验证你们的情谊吧,可惜,我却是看不见了……”他张开双臂,像要拥抱什么,整个人却向后仰倒,残云飞落般坠入渭河奔涌的急流里。
孟于飞怔怔地呆立了片刻,用剑尖挑起那幅泛着凄冷光芒的血月剑谱,看着,直到身后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
“江断雪呢?”君承宇望着他的背影问。孟于飞的手垂下来,不着痕迹地将那白绡笼入衣袖,然后回身一笑:“死了。”
“血月是剑中的鬼魅……”孟于飞痴看着手上的同风,“它能让你一天比一天更强,强得出乎意料,强到不愿意跟在任何人身后。欲望和野心,就是江断雪那个濒死之人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击,这一击摧垮了我的淡泊和本分——被人耳提面命几十年,也算是种本分吧……”
“耳提面命?”君行远淡淡重复,心却被什么揪了一下,“你和我爹几十年的兄弟,就只有这四个字作结么?”“沧溟山庄里没有兄弟。”孟于飞笑得惨淡,“从我把血月剑谱藏进衣袖的那一刻开始,孟于飞与君承宇就已经离心离德。更何况我原本也不过是他的马前卒……像你爹那样的人,又哪里需要什么兄弟?我杀他,或者他杀我,都是早晚的事情。沧溟山庄太小,人心又太大。”
沧溟山庄太小,西南剑盟太小——即使广大如天下,也容不得两个想要当主人的人……不是兄弟,便是死仇。
“你是君承宇和龙夕的儿子,沧溟山庄天生的少主人,一场意气之争就能将西南剑盟揽于麾下。却不明白这一切原是要踏着别人的白骨才能得到的,而一旦得到,又难免有一天会在别人脚下化为白骨……”
同风剑上血红色的微芒再现,倒映出满院血红色的灯影,杀意便在这剑光灯影里凝结。
君行远明白,没什么话好说了。
巡更人百无聊赖地穿过长街,不知道自己手上那半声竹梆竟成了沧溟山庄里一场决战的起始音符。这是九霄与血月的第三次对决,自然,也是最后一次。重剑在骤起的长风中嘶吼,划破一庭清寒刺向孟于飞。孟于飞的微笑里有点儿轻蔑也有点儿悲伤——这个孩子出剑的样子,竟和他父亲相差无几。
微笑消失的时候,青衫已贴着袭来的剑锋飘转开,幽灵般的步法中没有半点“人”的气息。君行远的剑刺入虚空,回声犹在耳,视野边缘同风剑的光华便暴涨起来。
苍白?妖红?灼热?冰凉?冶艳?肃杀?分不清楚——同风剑起,血月转腾,所有感觉在那血色月光中失了界限,入了梦魇。这,便是鬼魅的力量。
剑气如酒,让四下里的残灯都醉至癫狂,再于癫狂之间飘摇,于飘摇之间寂灭。灯如此,人也一样。几乎没人能在这样的剑意之下心静如水,而迷乱就意味着死无葬身之地。因此那一剑飞落时君行远在孟于飞的眼里已经等同于死人,一个像他父亲那样被贯穿了胸膛,滴血无存的死人。
然而,君行远忽然倒了下去。将死之人本来就该倒下,只是他倒得早了一点,姿势僵直而怪异,毫无美感,却刚刚躲过了那夺人心魄的致命一击。
血色剑光没入地上的青石,一瞬之间孟于飞脸上闪过些茫然和落寞,之后他听到衣袂腾风的声音,回首时,身后风雷万钧的一剑已经如天河乍泻,避无可避……那是九霄剑中最凌厉的一式,名字叫“王者之怒”。
——王者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什么样的仇恨不能结下,又有什么样的仇恨不能了断呢?
启明星在天际飘浮,孤独而苍白,星下东厢房的高脊上,江断雪和龙夕的衣衫已经被风露沾得湿了。
“我说过他不会死,这下放心了么?”江断雪问龙夕。
“小远那最后一式,是你教的?”
“当年你父亲就是这样战胜了我父亲。”江断雪微笑,“那场决斗,我可是唯一的见证呢。”
龙夕的目光从儿子身上转回来,幽幽地望了他很久:“你是个狠毒的人。”
“……什么?”江断雪佯装不解。
“无论血月还是九霄,其实都不够可怕,”龙夕说,纤细的手指点了点他的胸口,“最可怕的……是你的心。”
尾声
君行远在北郊的野店里没有找到江断雪和龙夕,四下里徘徊一番出来,却看见了门口站着的水红色人影。
“他们去江南看花了。”江眸儿说,“想去找他们?先打赢我再说吧。”一柄长剑亮出来,清光湛然,却又不是上次那把了。
君行远有些无奈:“你这样整日里比剑,换剑,难道不累么?”“我喜欢。”湖水样的眼波流转,转出些促狭和顽皮,“你这样整日四下寻仇,难道不累?”
趁君行远微微愣怔,红衣已挟着剑影飞来——又一场战斗开始了,在温暖的阳光下,和煦的春风里……
远处,黄尘古道上有人在唱歌,带着三秦乡音的荒腔野调,却高亢入云:“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古人墓;岸头沙,带蒹葭,漫漫昔时,流水今人家……”
(完)
侠世界微信公众号,中国最好武侠自媒体
每日推送一部优秀武侠原创中短篇小说
更有各类武侠典籍资讯周边信息推送
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社版权所有,如需合作
请联系158728590@qq.com
回复:相应节气,查看节气征文电子书
回复:定制书,查看武侠版独家**定制书
回复:试读,抢先看最近上市《武侠版》精彩内容
回复:刀剑江湖,查看往期原创小说
回复:江湖秘密,查看武侠知识
回复:江湖考场,查看武侠测试
回复:相应生肖,查看生肖征文电子
-
- 百度热搜
- 新浪热搜
- 1 匈牙利总理欢迎习近平夫妇来家里
- 2 热 福建舰也太太太太太太大了
- 3 热 男子因夹不住人字拖被查出脑瘤
- 4 9图带你走近匈牙利
- 5 热 杭州房产中介称电话被打爆
- 6 马克龙两天用中文连发四帖
- 7 这项链戴上根本不敢咳嗽
- 8 主播跨省帮取毒快递案终审仍判无期
- 9 门店坍塌救护车拉了七八车?谣言
- 10 戚薇回夏家三千金拍摄地感叹恍惚
-
热门文章
最新文章
随机文章
-
 原神去衣物图片(原神女角色黄本子)2022-06-18 阅读(259117)
原神去衣物图片(原神女角色黄本子)2022-06-18 阅读(259117) -
 长弓燧龙胡桃(原神)免费(长弓燧龙胡桃神里绫华禁动漫天堂)2023-03-19 阅读(199519)
长弓燧龙胡桃(原神)免费(长弓燧龙胡桃神里绫华禁动漫天堂)2023-03-19 阅读(199519) -
 雷电将军被淦出液体,原神雷电将军被ⅹ2022-07-15 阅读(190499)
雷电将军被淦出液体,原神雷电将军被ⅹ2022-07-15 阅读(190499) -
 原神女角色黄本子,xman每日好图原神2022-08-12 阅读(164719)
原神女角色黄本子,xman每日好图原神2022-08-12 阅读(164719) -
 关于原神八重神子正能量p图全光的信息2023-04-16 阅读(136131)
关于原神八重神子正能量p图全光的信息2023-04-16 阅读(136131) -
 原神女角色去掉所有服装的图片(原神女人物去掉所有服装)2022-08-17 阅读(134752)
原神女角色去掉所有服装的图片(原神女人物去掉所有服装)2022-08-17 阅读(134752) -
 原神vicineko在哪个网站(优菈大战丘丘岩盔王vicineko资源)2022-07-31 阅读(118551)
原神vicineko在哪个网站(优菈大战丘丘岩盔王vicineko资源)2022-07-31 阅读(118551) -
 原神魈空cp开车(原神变成小孩的空被各位)2022-06-17 阅读(112867)
原神魈空cp开车(原神变成小孩的空被各位)2022-06-17 阅读(112867) -
 原神女性角色去内无布料图片,原神诺艾尔去衣物图片xman2022-06-18 阅读(110836)
原神女性角色去内无布料图片,原神诺艾尔去衣物图片xman2022-06-18 阅读(110836) -
 原神旅行者趴在雷电将军身上,原神当雷电将军推到了旅行者2022-09-01 阅读(109179)
原神旅行者趴在雷电将军身上,原神当雷电将军推到了旅行者2022-09-01 阅读(109179)
-
 红包多多下载安装旧版(红包多多下载安装最新版)2024-05-09 阅读(3)
红包多多下载安装旧版(红包多多下载安装最新版)2024-05-09 阅读(3) -
 罗伯特霍里进名人堂了吗,罗伯特霍里2024-05-09 阅读(2)
罗伯特霍里进名人堂了吗,罗伯特霍里2024-05-09 阅读(2) -
 梦妆花萃透亮净白系列使用顺序,梦妆花萃净白保湿乳2024-05-09 阅读(2)
梦妆花萃透亮净白系列使用顺序,梦妆花萃净白保湿乳2024-05-09 阅读(2) -
 奢侈品平台哪个比较靠谱,奢侈品有哪几个可靠的网站2024-05-09 阅读(3)
奢侈品平台哪个比较靠谱,奢侈品有哪几个可靠的网站2024-05-09 阅读(3) -
 富勒烯水(富勒烯水光针是械字号吗)2024-05-09 阅读(2)
富勒烯水(富勒烯水光针是械字号吗)2024-05-09 阅读(2) -
 原神官网300万预约累计奖励,原神官网3.02024-05-09 阅读(2)
原神官网300万预约累计奖励,原神官网3.02024-05-09 阅读(2) -
 原神古云有螭(原神古云有螭攻略)2024-05-09 阅读(3)
原神古云有螭(原神古云有螭攻略)2024-05-09 阅读(3) -
 原神pc端怎么下载官服,原神pc官网怎么下载2024-05-09 阅读(3)
原神pc端怎么下载官服,原神pc官网怎么下载2024-05-09 阅读(3) -
 赚钱我的饭店(我的饭店赚钱是什么套路)2024-05-09 阅读(4)
赚钱我的饭店(我的饭店赚钱是什么套路)2024-05-09 阅读(4) -
 唯美嘉露,唯美嘉露手霜2024-05-09 阅读(3)
唯美嘉露,唯美嘉露手霜2024-05-09 阅读(3)
- 标签列表
-